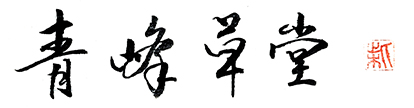
及时在线
柴德赓先生评书论人之卓识——读《史学丛考》浅议
《史学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出书之前,曾先后读过柴先生的某些文章,每读一篇,无不深受教益。迨至读此《丛考》,更在比较完整系统的意义上,了解柴先生一生治学著述之精华,即在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多方面的卓然造诣,令人敬慕。
柴青峰德赓先生之大著《史学丛考》,1982年出版,承柴师母陈璧子先生惠赠一册,至幸至感。
《史学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出书之前,曾先后读过柴先生的某些文章,每读一篇,无不深受教益。迨至读此《丛考》,更在比较完整系统的意义上,了解柴先生一生治学著述之精华,即在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多方面的卓然造诣,令人敬慕。作此浅文,以寄缅怀。
《丛考》共收文章二十七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历史人物和史学古籍的考述与评论。从标题所点人名二十(重复者不计),所点书名十三(包括碑记,信札除外),可见崖略。以“评书论人”四字概括全书,似无不可。对此,柴先生有精确的论证和卓越的见解。
从全书各篇,归纳柴先生在评书论人的标准:一是爱国思想,二是进步观点。据此两条在不同对象身上之不同表现(或有或无,或此或彼,或正或反),辨明人之臧否、书之高下、事之是非。柴先生为此不惮其烦地作了种种考证。这绝不是无的放矢,立异好奇。而是带着满腔激情,出于作为一个爱国进步史学家的使命感,为弘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发挥历史可净化人之心灵,可使人明智的社会功能,殚思极虑,作出的大有益于教育当今知识分子别是非、明劝戒、爱祖国、求进步的可贵贡献。
一、弘扬爱国思想
就爱国思想而言,按照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伦理观念,其基本精神,一在于“华夷之辨”,二在于“忠奸之分”。前者表现为坚守民族气节,为维护华夏文化,对来自某些民族上层征服者的破坏势力,拒不降服,抗争到底;后者表现为对高层统治集团内部倚仗皇权、严重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进行誓不两立的除奸斗争。《丛考》中有关这两方面爱国事迹的考述文章,涉及的人物绝大多数属于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涉及的书籍主要是《通鉴胡注表微》(包括《通鉴胡注》本身)。
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人物,其是否爱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视其对阉党,对清朝统治者,是反,是抗,是附,是降而定。这一时期,他们的爱国表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反对阉党;二是积极抗清,进行武装斗争,包括发动起义,扶持南明政权,兵败殉国等;三是消极抗清,以自尽、隐逸、为僧等方式,拒不出仕,坚不投降。这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严守“忠奸之分”、“华夷之辨”两个界限,坚持民族气节的实际行动。
为什么抗清是爱国行为?柴先生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解答。他认为对清朝统治者在“唐熙以后逐步建立统一国家,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必须给以很高的评价。但对于清初下江南的屠杀,文字狱的不断发生,满汉待遇的不平等,也必须批判。”这就是说,明朝遗民的抗清是反抗清初统治者对先进的华夏传统文明的野蛮破坏,是“当时的社会和形势所决定的”,应该肯定是爱国行为。
《丛考》中有关上述三方面爱国斗争的考证文章,主要有《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以下简称《事迹考》)、《〈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以下简称《谢三宾考》)、《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以下简称《弘储》)等三篇。这三篇文章体现了柴先生的苦心孤诣,如韩愈所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显隐表微,褒善贬恶,爱憎分明,情见乎辞。因而不仅具有令人心折的说服力,又有使人动情的感染力。这两大效应,通过文章中某些鲜明的特色而发挥出来。
特色之一,柴先生在文章中往往要说明作此文之动机或宗旨。如作《事迹考》是因为对那些明末留都南京一百四十多位共同署名发布《防乱公揭》,声讨漏网阉党巨魁阮大铖的年轻士子,“惜其力,哀其志,怜其遇”。认为这群士子“文章豪华,年少蜚声,皆具用世之才,怀救时之志,使胡马缓渡,明社稍延,则诸君者安知非庙党之器”!但事实却是“强者身逢大难,断头碎骨以死;即生者亦大半弃妻子,散家财,去乡里,或以僧死,或以隐死”。他们“一念故国,声泪俱下,人世凄凉悲惨之境,孰有甚于此者乎”!真是沉痛之至。柴先生怀此沉痛心情,写此考证长文。也可以说,这是柴先生写所有这类文章的总的心态。
由此心态而敬其人,而究其事。对此,柴先生的文章特重拾遗补阙,即“拾”记载中所“遗”爱国之人,“补”传记中所“阙”爱国之事。为“发潜德之幽光”,对爱国之人之事,越是“微”者“隐”者,越要“表”之“显”之。
“拾遗”之例,如《事迹考》中一百四十多人,其大多数属于记载所“遗”之“微”者,“甚者竟无一字之纪”。虽然如此,柴先生却竭力多方寻求关于这些人的爱国言行史料,如披沙拣金,搜剔爬梳,“虽片言只字,亦所珍惜”,终于使此等记之少,知之鲜者,事悉名传。而对于那些当时地位较高,“人各数传”,知之较众者,柴先生则认为虽记载“累篇盈牍,弃之不惜”。
“补阙”之例,如有人作《王嗣奭和他的〈杜臆〉》一文,对王嗣这一明朝遗老、八十衰翁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即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不肯屈节于清(不应召赴抗谒见清帅,不剃发,不穿清服),且深信祖国可复,竟漠然无所反映。柴先生不得不作《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一文以补此有关爱国言行之重要缺失。又如明末爱国和尚弘储,其一生最大事迹,不在于宗教活动,而在于坚守民族气节,帮助和联系众多明朝遗民,拒不降清。对此,因“文献脱落,弗能详”,“世不尽知”,故柴先生广征博引,作出考证详确的《弘储》一文,阐明了弘储及其所联系的若干明朝遗民的爱国事迹,补充了有些传记中对此记述简略含糊的缺陷。这种“补阙”对于真正了解那些奉佛遗民的光辉历史,弘扬其爱国精神,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对反面人物,因记载朦胧,以致其劣迹恶行模糊不清者,柴先生认为也必须弄清底细,露其原形。《谢三宾考》就是为此而作的。因谢三宾“其人徘徊明清之际,明清皆无传,又因诸家记载多隐其名,或异其称(各记载中共有二十多种异称,如夫己氏、降臣夫己氏、降臣、贼臣、降绅、逆绅、老奸、叛儿、逆竖等),故三宾之名反不著”。而此人“固晚明史上一重要人物也”,因为他是当时浙江鄞县一降清之官绅,曾公然与本乡起义抗清之广大士民为敌,用心险恶,几经破坏抗清斗争,陷害爱国志士,故有必要“钩稽其事迹著于篇”,使此“非寻常降人”,原形毕露,“诛奸谀于既死”以垂戒后世。
特色之二,三篇文章,不论其题名为何,其内容实际上都是多人合传。但这种合传并非一人一传的简单配合,而是诸人相互关系、共同事业的既析又综若浑然一体的整合。它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一幅幅士大夫人物的群体活动画面,显现了那个时代风云变化中一股股激浪沸流。《事迹考》显然就是这样一篇合传文章。它把所考证的一百四十多人作为一个群体,以人系事,“因事分类”,进行阐述。从所分二十多个事类中,我们看到属于反阉党和抗清斗争的种种表现者占了大部分,从而得知这一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既是反阉党的坚强斗士,又是积极或消极抗清的民族脊梁。他们从反阉党到抗清,正是抗清殉国英烈瞿式耜所说“平时有直谏敢言之气,则临难有仗节死义之臣”(《瞿式耜集·存公论重言官疏》)那句名言的印证,具有发人深思的垂训意义。
《谢三宾考》与《弘储》两文,名为“个传”,实仍为“合传”。前者通过考证与揭露谢三宾破坏抗清斗争的罪行,突现了当时以鄞县为中心的浙东一带爱国官绅士子,互通声气,休戚与共,同举义兵,遭谢陷害,壮烈殉国等英勇事迹,文中涉及的爱国志士粗略估计约有六七十人。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目标一致,为抗清而奋起战斗,甘洒热血的遗民群体。后者以弘储的爱国事迹为轴线,详考弘储及其弟子和其他遗民之间的互助互励关系,以及他们的高风亮节懿行。文中涉及的爱国志士粗略估计约有五、六十人。那许多遗民也实际上形成了又一种目标一致,以弘储为首的,为反清而隐身遁形,坚贞守节,誓死不降的遗民群体。这一群体中的弘储遗民弟子,自明朝大官(如东阁大学士熊开元、户部尚书张有誉、江西巡抚郭都贤)至举人(徐枋)、秀才(董说、王廷璧)均有之,或为祝发僧人,或为白衣居士。弘储所倡“以忠孝作佛事”、“忠孝实自佛性中来”,成为他们的共同信念。因为这里的“忠孝”,按照柴先生的解释,在民族矛盾时期,其意义“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是民族气节。遗民的‘忠’思想便是对异族坚决不投降,保全气节”。如何保全气节?他们的行动感人最深的莫如和降清仕清的士大夫人物严格划清界限。如徐枋在出家前,隐居灵岩山间,卖画自给,终身不入城市。“槁木形骸十六年,虽戚友罕睹其面”。“独处一椽,而床床屋漏,几废坐卧”。其故友仕清任江苏巡抚之汤斌,曾“屏从骑两次访之,终不得见,”欲馈以“一丝一粟”也不能达。只有弘储赠药捐粮以疗其病与饥,并在“山头困乏之际”,为他建一可栖之居,他恳辞不得,始感而受之。由此而祝发师事弘储,结成肝胆相照的密切关系。弘储另一祝发弟子郭都贤,在明朝曾奏请起用坐事落职之洪承畴,有恩于洪。洪降清后,曾访郭,虽得见,但馈金及拟提携郭子,均被拒。当时郭“故作目眯状”,洪惊问“何时得目疾”,郭答以“吾识公时”已有此疾矣。意为眼有疾而看错了人。洪会其意,只能默然。这位曾任明朝大官的佛门弟子郭都贤,“茹苦无定居”,漂泊于苏、鄂、湘等省之间,实无异于一游方僧。还有一位生于豪富世家的沈麟生出家后,也是“手担一襆被,徒步数千百里,雨则跣而行,往来吴越诸山”。这些就是遗民们艰苦守节之典型事例。他们对降清仕清者既是恨之鄙之,从而拒之避之,唯恐不及;而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则以弘储为首,相砺以节,相濡以沫,联系密切;即使分居各地,也常有诗文书札往来。弘储对那些曾任明朝某官之弟子,在文字上常以原官名相称,表明不忘故国。弘储又曾集若干僧俗遗民于灵岩山聚会,柴先生文中考出记有名姓之参加者约十人。其中有来自浙东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及其弟宗炎。这些遗民绝大部分是东林党人后裔,正如黄宗羲诗中所说“同是前朝党锢人”,他们“纵谈七昼夜”。所谈内容自然不会外传和留下文字记录,但从黄宗羲诗句“狂言世路难收拾,不道吾师(指弘储)狂绝论”,不难想见所谈崖略和忧国忧民、慷慨悲愤的心怀。这次聚会集中地反映了清初长江以南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弘储为首的彼此联系密切的僧俗遗民群体,这一群体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特色之三,为使善晋是非之别更若泾渭分明,柴先生文中往往出现正反对比性强烈的鲜明事例,《谢三宾考》一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略举其中数例如下: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至浙江,下令剃发,召各地明朝官绅来降。谢三宾立即往杭州谒见清帅,表示归顺。而与之“往还甚密”之同县友人祁彪佳则拒绝前往谒见,自投池中,以死殉节。
此时鄞县年轻士子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毛聚奎倡议起兵抗清,诸书称为“六狂生起义”。众推公绅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并请驻定海总兵王之仁带兵来会。但谢三宾也派人致书王之仁,以千金为饵,诱王杀六狂生与钱肃乐,破坏起义。此阴谋旋即为来鄞聚会之王之仁揭穿。三宾几被杀,哀请输万金得免。
浙东各地纷纷起义,支持明朝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立抗清政权。谢三宾行贿居然窃取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辅臣高位。但不久义师失败,鲁王入海,谢三宾却又迫不及待地率领朝中大官八十余人再次降清。而过去曾与谢三宾同建讨平登、莱叛军之功,都曾私分所获敌资数百万金之朱大典,此时既已“破家举义,尽其财不私”,又死守金华,“力竭不支”,在焚死眷属十七口之后,自尽殉国。
鲁王政权虽败,浙东仍有义师散据山寨坚持抗清斗争。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以华夏为首的鄞县诸乡绅密约舟山总兵黄斌卿及各处山寨义师,定期进攻为清兵所占之宁波城。其致大兰山寨(浙江余姚县南)之帛书途中为谢三宾使人赚取,以此向清吏告密,乃至诸路义兵为清军所阻,内应外合收复宁波城之密谋未成。倡仪者华夏、王家勤、杨文琦、杨文瓒、屠献宸、董钦等六人,因谢三宾告密,先后被捕就义,称为六君子或六烈士。其实谢三宾所告密者不止此六人,三次告密共十五人。六烈士之外,余则或逃,或被捕因里中义士以金帛力救而获释。
华夏等入狱后数日,谢三宾因清吏欲诈其家财亦被捕,与华夏同受审讯。“谢频叩地,称述清功德”,表已推诚归顺,不敢有异心,“摇尾乞生,万分狼狈”。清吏使人密语华夏攀引三宾,但华夏则大义凛然,严辞斥责三宾“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此好事(指起义抗清),岂有他分?惜与他同狱,未免抱愧耳”。谢闻华言,厚颜向华稽首,连声称谢:“长者,长者!”他总算出狱了,但他的巨万家财也为之消耗殆尽了。
以上所述,就是柴先生为弘扬爱国思想所作几篇出色考证文章之要义。其论人如此,评书亦然。所作《〈通鉴胡注表微〉浅论》(以下简称《浅论》)一文,阐明了他的老师、当代大史学家陈援庵(垣)先生如何以及为何作《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表微》),从而弘扬了陈先生乃至《通鉴胡注》作者胡三省的爱国思想。有点有三:
(1)陈先生是第一个真能了解胡三省的人。了解什么?主要是胡三省的爱国思想。胡三省生当宋末元初,是一位坚贞不屈、苦志守节、隐居山中的南宋遗民,宋元各史均无传,生平事迹不显示;他注《通鉴》颇多含蕴爱国思想之微言,却从无人注意,正如陈先生所说:“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有若无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无人知“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所以说胡三省是一位“在长时期被埋没着”的爱国史学家。直到六百六十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才被当代史学大家陈先生所了解,作出《表微》,使胡三省的生平、处境、抱负、治学精神,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大白于天下。
《表微》首先表出胡注中不忘故国之深情,盖“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当时元朝已有“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之令,但胡注中对宋朝和宋帝仍常用昵称或尊称,如“我朝”、“本朝”、“国朝”、“我宋”、“皇宋”、“吾国”、“我太祖皇帝”、“我朝太祖”等等。虽然其中为元末刻版时改了不少。但改刻所遗者仍多处可见,《表微》中都列举出来了。
不仅如此,《表微》还进一步对胡注中寄托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隐有所指的评论和感慨,作了探析,表出其不言之深层含意。如对宋朝政治腐败招致灭亡和权奸败类卖国投敌之斥责、对南宋恭宗和太后奉表出降,辱身臣妾之伤悼、对元朝残暴统治之申诉、对人民反民族压迫斗争之同情、对华夷之辨、民族意识之强调,以及自己坚贞守节,矢志不渝之决心,等等。凡此均表明陈先生对胡三省爱国思想之充分了解,否则不可能作出如此确切的“显隐表微”。
(2)陈先生为什么要作《表微》?怎么能够那样确切了解胡三省的爱国思想?这可从陈先生作此书之时间和当时的处境而得知。陈先生变到:《通鉴胡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元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年);而在六百六十年后,亦在乙酉(1945年),即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八年,《表微》成书。前后两“乙酉”,陈先生在1945年7月为此书所作《小引》中说是“偶合”。柴先生认为这是在沦陷时期不得不如此说。实际上这个时间的选择正是陈先生的本意所在。“刊本有先生自识,已经明说此论文为纪念被捕(指中国教授与学生)及被俘(指英、美、荷等国教授)诸友而作”。陈先生在1957年《表微·重印后记》中开宗明义就指出:这部书“是抗日战争时我在北京写的”,表明他当时置身敌人铁骑下的沦陷区,与胡三省的亡国处境相同。所以他说:“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于是决心对胡三省其人其书,作了全面的研究,从而明其爱国赤忱,知其不言微旨。一言以蔽之,处境心境相同,如柴先生所说陈先生离胡三省“近”,故能“冥契作者之心”也。
(3)柴先生在《浅论》中说,“在北平沦陷期间”,陈先生常常提倡“有意义的史学”,《表微》正是这样一部“有意义的史学”巨著。“意义”即在于弘扬爱国思想。柴先生认为陈先生并“不专恃考据”,而是在考据作出客观论断之外,还要对历史事实作出精确的解释,所以柴先生又说:“《胡注表微》这部书,在考证的工夫上看,陈先生自然当行出色,在解释历史的一点上看,陈先生确有独到的见解。陈先生是思想、学问、生活打成一片的人,不是徒发空论的。”这也就是说,《表微》乃是陈先生的爱国思想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亦即观点与考证统一的成果。
总之,从《通鉴胡注》到《通鉴胡注表微》、到《〈通鉴胡注表微〉浅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古今史学家的爱国传统美德,世代增辉。
二、显彰进步观点
《丛考》中柴先生说:清代王鸣盛与钱大昕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范畴,“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职志”。又说:“章学诚是封建社会的文士,他著的书必然代表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这种阶级烙印,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所不能免的,可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这些论点当然适用于所有封建社会的文士。其中所谓“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见解,告诫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不同对象,作出具体分析。柴先生由此辨明了某些人和书在当时的思想学术上的进步观点,从某些人的“无声之声”中,从某些人的不被人了解或遭卫道士歪曲、恶言攻击的言论中,“显”其进步观点之“隐”,“表”其进步观点之“微”;用对比方式,把进步观点从僵化思想中区分出来,《丛考》中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其所论述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问题:
其一,关于尊王问题
在封建专制下,“尊王”与“忠君”是天经地义。《春秋》宣扬尊王,历代修史皆奉为圭臬。但各史为此而作之说教,未必千篇一律。如《丛考》中《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两文,对两部史学名著,分别作了评析。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尊王忠君原则问题上,观点同而有异。
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全仿《春秋》,突出“尊王”,强调“忠君”。他对五代诸帝虽多无好话,但宣扬无论国君如何,“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忠于一主,不可失节”。如对梁朝,一方面恨其篡唐,另一方面又教人忠于其君。认为“即使象五代那样君不君、父不父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臣不臣、子不子”;还认为“即使‘夷狄’入主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书中对五代大臣之褒贬即全以“忠君”为准,其列传分类体现了这种褒贬精神,如将专仕一朝者列入这一朝的大臣传,将历仕数朝者列入杂传,分别寓褒意和贬意,即所谓“寓褒贬于体例之中”。这是出于教条式地模仿《春秋》书法,直接为宋朝统治服务之目的,维护宋得国于五代,前后一脉相承之正统地位。如此绝对化的、僵化的“忠君”思想,作为一种史学观点,柴先生认为是“非常有害”的。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当然也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宣扬“尊王”与“忠君”。其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其书并非专学《春秋》人褒贬上下工夫,而是比较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不是从教条出发,通过占有大量史料,辨其同异真伪,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供人君治国安民,巩固封建统治之用。所以书中对政治十分腐败,甚至“伤天害理,残民以逞”,丑恶不堪入目之事,也不厌其详地记述。这在主观上是为了借此进谏诤,作鉴戒,敲警钟,筹对策;客观上却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阴暗面,而且事实上阴暗面的材料大大地超过了光明面。对农民起义的记述当然不可能摆脱地主阶级的根本立场,称“寇”称“贼”,口诛笔伐,自在意中。但其对农民在起义前受官吏的残酷剥削,不能生活下去,被迫起而反抗的记叙,却还不离事实。书中议论固有“事君”之道,也有“为君”之道,其开宗明义第一篇议论,即认为“三晋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据此引伸言之,礼法之坏,坏自天子,治乱兴亡,始于君道,乃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看来其书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写起,是具有深意的。我们不妨说,同是尊王忠君,《新五代史》只讲君之“权”的一面,只要求臣下“尊”君“重”君;《资治通鉴》则除此之外,还讲君之“责”的一面,还要求君上自“尊”自“重”。两相对比,后者之较有进步性,不言可知。
其二,关于正统问题
对这一问题,柴先生很赞成司马光修《通鉴》所持观念。此观念含意有三:①“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这就是说,非统一天下之天子既无天子之实,则其王朝即不能称正统;唯统一王朝始有正统地位。②“天下离析之际”,取某一国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但离析之局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民族建国并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对此,《通鉴》取东晋、南朝年号,不是仅为了“借其年以记事”,而是在实质上否定了隋唐以来以北族为正统的观念,确认了东晋、南朝的正统地位,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应据夷夏之辨的民族大义以华夏王朝为正统。③另一种情况是并立诸国同属华夏,如三国那样,则不分什么正统与非正统,用某国年号才是真正地“借其年以记事,非有所取舍抑扬也”。
所以柴先生总结说:“居今日而论正统,舍统一与夷夏二事,一切可以不谈。王莽也,武后也,曹操也,刘备也,彼皆中国人也,司马温公所不欲深谈,固不必推波助澜,为古人争是非也。”
观此可见,柴先生肯定了《通鉴》中以统一王朝和华夏王朝为确立正统的标准,因为唯此二者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华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即柴先生所说“一曰谋国家之统一,二曰严夷夏之大防”,具有重大意义。古史典籍凡按此标准处理或评论正统问题者,则是正确的,否则便是谬误。
《丛考》中《〈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一文即是柴先生对谬误正统观念的批判。柴先生认为“清修《四库》,名曰右文,实为禁书”。“凡直接抵触清室之书,既已禁毁无遗,其余著录存目之书,馆臣不能一一删改,辄于《提要》微发其意,正统问题其尤著者也”。正统问题,历代所争,无不出于为当时统治服务之目的。对此,《提要》作者尤为“积极”,表现于对清朝统治者,极尽其“谐臣媚子”之能事,超越前朝,莫此为甚。其正统观念主要见之于对某些史书古籍(多数属明朝,少数属南宋)之抨击,其矛头所向之史:一是以宋包举辽、金者(如《宋史新编》、《宋史纪事本末》),二是以南宋最后称帝之二王即广王昰与益王昺列于帝纪以存宋统者(如《宋史新编》),三是以元朝建立前蒙古兴起史事属宋,元顺帝败退蒙古后史事属明者(如《元史纪事本末》),四是记明太祖洪武纪元前诸事不用元年号(如《昭代典则》),以及贬低元朝(如《世史正纲》),乃至不以元为正统者(如《宋史质》)。其意图在于①扬辽、金抑宋,即所以护清抑明;为辽、金争正统,“意在扶立异族,为清室道地”也。②否定南宋二王残统,即所以否定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残统也。如肯定前者即不能不肯定后者,是则必影响清顺治一朝之正统地位。③维护并上推下延元统,为元亦所以为清而抑宋、明也。
总之,《提要》作者,“凡涉宋、辽、金、元、明、清国统者,均有一贯之主张”,即反对“严夷夏之大防”的正统观念。此种正统观念,在“民族思想远胜前代”的明朝诸文士的著述中,反映特别强烈,故《提要》着重抨击之,不遗余力,意在消除民族思想,以利清朝的统治。其影响是有害的。
其三,关于尊经问题
封建时代,儒家六经居于独尊地位,儒者之徒必然尊经,历代如此,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丛考》中有柴先生研究评析王鸣盛、钱大昕、章学诚、汪中等人学术与思想的几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四个人在尊经问题上的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意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尊经复古与通经致用的分歧
四人中,王鸣盛与章学诚主尊经复古论,钱大昕与汪中持通经致用论,恰好两两相对。
王鸣盛宗吴派经学,主张求古、尊古,认为“求古即所以求是”。故其尊经要求一切从古,“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斥责王安石作《三经正义》,违反汉人家法,罪不容诛。他所著《尚书后案》,即“完全以尊崇马融、郑康成之学为目的,无新思想可寻”。他以为治经“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如此而已。所以柴先生批评王鸣盛尊经、治经,是“极端抱残守缺”、“复古倒退”、“为古人作奴隶,引导大家往死胡同走”,“对中国文化的进步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章学诚以六经为“宗本”,认为六经尊严,不容丝毫有所侵犯,六经不可议,孔孟不可非,朱熹也不可议。他绝对相信已有多人怀疑的《周官》、尊崇周公,美化古代。其尊经复古之僵化思想与王鸣盛并无二致。柴先生鉴于对章学诚“近来肯定的过多了些,批判则太少了”,故而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大异于过多肯定的正确评价。应该说,章学诚的根本思想是复古的、僵化的,这是他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上曾否起过进步作用的关键所在。
通经致用论当然也尊经,但非唯古是求,唯古是尊,而是比较实事求是,尊而不悖历史真实,通而不离致用救时。如汪中以为孔墨之争,“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二家平列,不分尊卑,历史原是如此。他又以为儒墨之学可相互补充,对墨学岂可完全摒弃?他说:“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哀世之弊。”“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这是反对孟子对墨子的攻击,对墨学估价尚较平实。他还反对妇女“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守“望门寡”之节,对当时“以礼杀人”之礼教提出了正面的批评。汪中的这些议论遭到了在后世比他名气大得多的同辈人章学诚的诋毁攻击,柴先生正确指出:章所反对者,“恰好是汪之可取之处”,在当时是极大胆的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所以柴先生连声称赞说:“不可谓无‘识力’。”“‘识力’是过人的。”对此,柴先生能辨而明之,也足以表明其“识力”之不凡。
钱大昕也通经学,也受吴派经学影响,但他不专治一经,亦不专守汉儒家法。他和汪中的关系很好,也有象汪中那样妇女可改嫁的主张。讲经学也能针对社会某些问题而发,但较隐蔽,如作《大学论》和《皋陶论》就是批评商贾献资、官吏罚俸、惩治罪吏诸时政的实质弊害的。他还很佩服皖派经学开创人戴震,对戴所说“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那种谴责清朝统治的话,不仅能接受,而且起了共鸣。不过,钱大昕那些较进步的观点不能象戴震与汪中那样露骨表达出来,其通经致用思想,是柴先生经过细心读书,于钱之“无声之声”处,结合钱之交友关系和当时政治情况,融会推考而发现和体会出来的。
章学诚也好谈经世之学,“后人也从这方面赞誉他”。其实“他的思想是以拥护当时的封建统治为唯一职志”,与时政得失不敢有丝毫联系,殊无致用救时之意义,与其所攻击的汪中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2)尊经与重史的分歧
清代乾嘉年间,把治经看作是第一等学问,史学是被看作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当时一般文士大致均作如是观,但也开始出现抬高史学地位的主张。王鸣盛和钱大昕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畸重畸轻之分歧。
王鸣盛和钱大昕是同乡(嘉定)、同学、同年(同年中进士)、同官,又是至亲(钱是王之妹婿),特别是晚年同住苏州,各做一部内容大致相同的史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因此,历来人们总是把他们相提并论,特别是在史学成就上,视为同一类型,难分彼此。但柴先生把二人作了全面的对照,发现彼此对经学、史学的态度有守旧与立新,即轻史与重史之别。
王鸣盛,就其著述来看,经史参半,而当时人所重视他的仍在经学,认为他的成就在于《尚书后案》。可见王鸣盛虽治史也有建树,但其基本态度仍不离重经轻史之旧轨。钱大昕则大不然,他把经学和史学列于同等重要地位,这实在已经提高史学的地位了。他反对“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批评看不起史学的经学家。对此,柴先生誉为“竹汀(大昕字)出而形势一变”。他的学问主要是史学,其余各种专门知识,兼收并蓄,都是为史学服务的。虽然他和王鸣盛都是从经学的考据到史学的考据,但其史学著作多于王鸣盛,专精亦过之。他是以治经方法治史,又专治史而不专治一经的第一人。他和王鸣盛同而不同即在于:王固守传统,钱志在立新。立新就是把史学提高到与经学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对于文化的进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的命题,似乎也是重史。但其精意则在于六经乃最高标准之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故柴先生认为他“名为尊史,实则尊经”,即仍不失其尊经复古之“宗本”,与钱大昕之重史绝不相同。
三、学典范,守师训,继师志
《丛考》所收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我以为此文排在最后似有追本穷源,作为全集评书论人总结的意义。从评书论人的两条主要标准爱国思想和进步观点来看,柴先生的老师、当代大史学家陈援庵(垣)先生乃是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继往开来的崇高典范。他的爱国进步思想体现在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青年、热爱教育事业、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爱国思想和不断求进步的热情,更加显著地表现了出来。他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处于“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的危境,始终以一腔热爱祖国的赤忱,坚持民族抗日立场,充分发扬了坚贞不屈的精神。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向师生提倡“有意义的史学”,即弘扬爱国思想的史学;一面自己身体力行,潜心写出“有意义的史学”巨著,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积极抒发民族抗日情感,鼓舞人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陈先生在北平援救了因反饥饿、反内战而被捕的学生。北平解放前夕,他坚拒反动政府接其南下的威逼利诱,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心里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柴先生说陈先生“是一个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人”。在不断进步中,他以八十高龄的老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批准,终于找到了真理,批到了光荣的归宿。这一历程表明陈先生从一个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发展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谓“继往开来”,意义在此。可以认为:《丛考》中关于评书论人的两条主要标准,就是柴先生受了这一崇高典范的熏陶,得到启迪,从典范的高德懿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
柴先生说:“陈先生是思想、学问、生活打成一片的人,不是徒发空论的。”他在教育科研事业上数十年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诸如柴先生所举“教学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常亲自教基础课”、“以狮子搏象的力量来备课”、“讲解时一字一句从不放松”、“对同学的作业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要求同学也很严格”、“上课要指名提问”、“布置作业一定要按时交”、“对青年的鼓励与关怀无微不至”、“治学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重实践”、“总是半夜四点钟起来读书写文章,几十年从不间断”、“他的学问是多方面的”,而治学态度则虚怀若谷等等事例,无不熠熠生辉,令人肃然起敬,深受感动。柴先生说他在老师陈先生的身边亲灸的时间有二十多年。他确实不负老师的栽培,勤奋耕耘,做到了学典范,守师训,继师志,结出了集中反映于《丛考》中各篇文章的丰硕果实。柴先生在那篇纪念老师的文章中,表达了饮水思源,感激恩师的至诚,最后还说:“我要永远向老师学习,做他的小学生,踏着他所走的道路前进。”
作为这篇浅文的结语,作为读《丛考》的最深感受,我们要认真地向陈援庵先生和善继师志的柴青峰先生学习,他们永远是知识分子爱国家、求进步的表率楷模!
1990年7月写成于苏州大学
 Chai Niandong
Chai Niandong 内容编辑
内容编辑